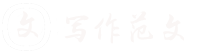历史典故:夏殷的“左右”问题 《史记孙子吴起列传》“夏桀之居,左河济,右泰华,伊阙在其南,羊肠在其北,……修政不仁,汤放之。殷纣之国,左孟门,右太行,常山在其北,大河经其南,修政不德,武王杀之”这是解决夏代地望的一条重要线索,集解瓚曰:“今河南城为直之……
历史典故:夏殷的“左右”问题
《史记·孙子吴起列传》“夏桀之居,左河济,右泰华,伊阙在其南,羊肠在其北,……修政不仁,汤放之。殷纣之国,左孟门,右太行,常山在其北,大河经其南,修政不德,武王杀之”这是解决夏代地望的一条重要线索,集解瓚曰:“今河南城为直之。”皇甫谧曰:“壶关有羊肠阪,在太原晋阳西北九十里。” 索隐刘氏按:纣都朝歌,今孟山在其西。今言左,则东边别有孟门也。很显然皇甫谧认为夏代地望在今天山西一带;但是没有明确夏代、殷商的左右问题。
在《尚书·汤誓·注疏》中引用吴起这段话,同时引《地理志》云:‘上党郡壶关县有羊肠坂,在安邑之北’。是桀都安邑必当然矣。
从《汤誓注疏》里面我们也可以发现古人对夏桀、成汤的都邑问题已经有怀疑,但是没有给出确切的答案。现代人几乎都认为“左为东,右为西”,这几乎成为确定“二里头遗址是夏代都城”重要依据。
事实上如果按照商代的东为左解释夏代的左右问题,《史记》中记述的很多资料无法形成证据链,甚至出现相互矛盾。比 如:
《史记·殷本纪》“古禹、皋陶久劳于外,其有功乎民,民乃有安。东为江,北为济,西为河,南为淮,四渎已修,万民乃有居”――这是大禹时期或者夏代的大致地望。有学者认为这个范围在古河济地区【今天的菏泽、濮阳、商丘北】,这样古九州在什么地方?
《史记·孙子吴起列传》“夏桀之居,左河济,右泰华,伊阙在其南,羊肠在其北”――如果左为东的话,河在夏桀东方;与前文“西为河”明显存在矛盾。当然也有人会提出这是夏桀迁都的结果,我以为这样的说法太牵强。
《史记·货殖列传》“自鸿沟以东,芒、砀以北,属巨野,此梁、宋也。陶、睢阳亦一都会也。昔尧作成阳,舜渔於雷泽,汤止于亳”――司马迁清楚的告诉我们尧、舜、成汤的地望在这一带,为何没有谈到禹的地望?可能有人会引用“唐人都河东,殷人都河内,周人都河南”“ 颍川、南阳,夏人之居也”反驳我的看法,我要告诉大家的是“河东、河内、河南”是各自都的位置,并且河虽然都是同一条黄河,但是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流向存在差异;而颍川、南阳是夏人居住的地方,与大禹的都城没有任何关系。如果大禹的地望在四渎之内的话,同样也与尧、舜、成汤的地望相吻合。
《史记·封禅书》“昔三代之皆在河洛之间,故嵩高为中岳,而四岳各如其方,四渎咸在山东”――三代之皆在河洛之间几乎是现在学术界认定二里头遗址是夏代都城的重要依据。如果考虑到大禹治水的范围在四渎之内的话,我猜测在四渎之内可能有伊水、洛水存在,只不过随着时间的流失,四渎之内的伊水、洛水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现在的伊水、洛水。我想“三代之皆在河洛之间”这句话本身是正确的,但是应当认识到“河洛”可能有变化。这里的山是指嵩山,如此四渎在嵩山东完全是正确的。
如何才能解决上述问题哪?只有从古籍中寻找。
《礼记·王制·注疏》中记述“有虞氏养国老於上庠,养庶老於下庠。夏后氏养国老於东序,养庶老於西序。殷人养国老於右学,养庶老於左学。周人养国老於东胶,养庶老於虞庠,虞庠在国之西郊。”(皆学名也。异者,四代相变耳,或上西,或上东,或贵在国,或贵在郊。上庠、右学,大学也,在西郊;下庠、左学,小学也,在国中王宫之东;东序、东胶,亦大学,在国中王宫之东;西序、虞庠亦小学也,西序在西郊,周立小学於西郊。)
列表如下:
有虞氏:上庠-大学-西-郊;下庠-小学-东-国
夏后氏:东序-大学-东-国;西序-小学-西-郊
殷人:右学-大学-西-郊;左学-小学-东-国
周人:东胶-大学-东-国;虞庠-小学-西-郊
如何界定贵右、贵左的问题,古人在《礼仪·乡射礼·注疏》中说的很清楚:云“周立四代之学於国”者,案《王制》云:有虞氏上庠下庠,夏后氏东序西序,殷人左学右学,周人东胶虞庠。周立四代者,通己为四代,但质家贵右,故虞殷大学在西郊,小学在国中。文家贵左,故夏周大学在国中王宫之东,小学在西郊。【作者注:虞殷贵右,右在西,左在东;夏周贵左与虞殷相反,因此左在西,右在东】
这里引用的贵左、贵右的问题与《礼记·曲礼上》“席南乡北乡,以西方为上”的贵左、贵右是一致的,《礼记·曲礼上·注疏》这样写道:
“席南乡北乡,以西方为上”者,谓东西设席,南乡北乡,则以西方为上头也。所以然者,凡坐随於阴阳,若坐在阳则贵左,坐在阴则贵右,南坐是阳,其左在西,北坐是阴,其右亦在西也,俱以西方为上。
不过我们也注意到在《白虎通义》中关于文家与质家的问题:在《白虎通义·嫁娶》中这样写道:“质家法天尊左,文家法地尊右”;在《白虎通义·爵》中“质家者据天,故法三光;文家者据地,故法五行”―――这里的记述与《礼》注疏的文家与质家是不同的,也与《史记》中记述“正月上日,舜受终於文祖。文祖者,尧大祖也”不符,我们看看《五帝本纪》记述尧的第一事迹是关于“天”的认识,舜则主要是关于“地”的认识。但是在《夏本纪》中禹则是主要对“地”进行的,至于夏我们无法得出结论;以后的商周也不能得出。不过如果从商王的名字使用天干的问题看,商应当是注重“天”的认识。―――关于文家与质家的问题是一个比较麻烦的事情,我们认为《白虎通义》的观点牵强一些。因此,采信《礼》的注疏,这一点希望大家注意。
按照中国的“贵”规则,得出的结论是:有虞氏、殷人西为右,夏后氏、周人东为右。
再根据《礼记·王制·注疏》记述:
曰:养於国与养於学文相对,故知国亦是学也。六十少於七十者,六十者宜养於小学,七十者宜养於大学,故云“国,国中小学”。云“在王宫之左”者,据上文而知。云“小学在国中,大学在郊,此殷制明矣”者,以上文云“小学在公宫南之左,大学在郊”,下文云“殷人养国老於右学,养庶老於左学”,贵右而贱左。小学在国中,左也;大学在郊,右也,与殷同也,故云“此殷制明矣”。以此篇从上以来,虽解为殷制,无正据可冯,因此小学大学是殷制不疑,故云“明矣”。
通过上文的讨论我们知道在有虞氏、夏后氏、殷人、周人时期贵左、贵右是不相同的;且周人、夏后氏与殷人、有虞氏左右是相反的。
如果我们的推测是正确的话,夏桀时期西为左,殷纣时期东为左。――很可能贵左、贵右以及涉及的阴阳是对黄河而言的,夏后氏、周人的都城在黄河以南的话,属阳,其左在西。而有虞氏、殷人的都城在黄河北,属阴,其右在西。这一点可以参照 ——“席南乡北乡,以西方为上”。即使是现在我们也遇到这样的语句“某某城市坐落在什么地方”,既然是坐就应当有相近的属性。如果这种推测合理的话,可以帮助我们找到夏后氏的都城,也可以帮助找到有虞氏的都城。
如果关于夏后氏、殷人的左右分析是正确的,那么再重新看“夏桀之居,左河济,右泰华,伊阙在其南,羊肠在其北、、、殷纣之国,左孟门,右太行,常山在其北,大河经其南”我们就会发现古人这些话并没有欺骗后人。
下面我们看看《史记·殷本纪》中记述的夏禹的地望:“古禹、皋陶久劳于外,其有功乎民,民乃有安。东为江,北为济,西为河,南为淮,四渎已修,万民乃有居。”这里的济在北与左河济的济有不同,很可能是在禹时期与夏桀时期有变化的结果;但是河是一致的――即夏的地望在开封向淮阳一线或者古鸿沟一线的古黄河东边。
当然有虞氏、夏后氏、殷人、周人的贵左、贵右也可能与他们最初居住地的环境有关,鲧、禹很可能与水有关,因此河为贵;帝喾高阳氏,崇高,与山有关因此太行为贵。
究竟为何会出现有虞氏、夏后氏、殷人、周人时期贵左、贵右不同这种现象,也许有其他我们不知道的因素。但至少可以肯定夏代与殷商的左右是不同的!
另外在《史记·殷本纪》中记述“伊尹去汤適夏。既丑有夏,复归于亳。入自北门,遇女鸠、女房,作女鸠女房。”《尚书注疏》对鸠、房解释是,二人汤之贤臣。由此我们推测北门在成汤没有称王以前仍然是夏代,按照夏代贵左的原则,北门是正门。也许就是这个因素,所以伊尹、鸠、房这些成汤的大臣才会在这里“遇”,按照《尚书注疏》的对“遇”的解释是“不期而会曰遇”。很显然,伊尹在北门遇到鸠房并不是事先预订好的。既然没有预订,成汤的大臣都在北门进出就说明这个方位是正门。似乎可以进一步证实夏代贵左的事实!【很明显成汤、夏桀时期已经有都城,并且正门是北门;而二里头遗址没有发现城墙】
再根据《史记·周本纪》“周公行政七年,成王长,周公反政成王,北面就群臣之位。”这里的北面,与《史记·夏本纪》记述“禹於是遂即天子位,南面朝天下”是一样的道理,周公时期“北面就群臣之位”臣在北面,禹为天子,在南面。总之王与臣位置是:王在南,臣在北!
如果成王、大禹召见大臣是面北的话,与《礼仪·乡射礼·注疏》中的“文家贵左”,西为上是一致的。如果将来发现周朝、夏代的宫殿遗址的话,我们将从遗址的大门在北面证实这件事情的真实性。
如果不清楚夏代与殷商的左右不同,就无法理解《史记》中记述的尧、舜、禹、夏桀与成汤、殷纣的地望的左右问题;就会怀疑古人记述的是否存在问题。也许将永远无法找到真正的夏代的地望与都城,如此中国的历史将不可能得到国际学术界的认可。
归根到底,左、右问题实际上是中国古代的阴阳问题,对方位的左右的变化是阴阳的具体运用而已。